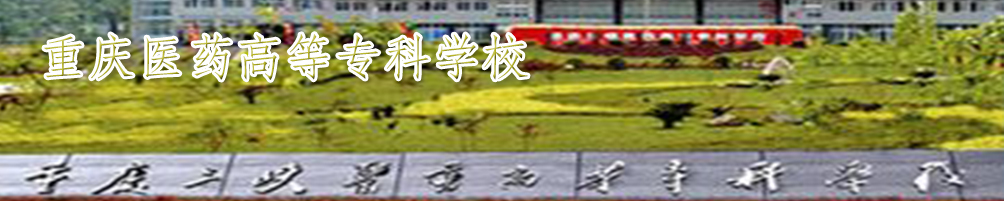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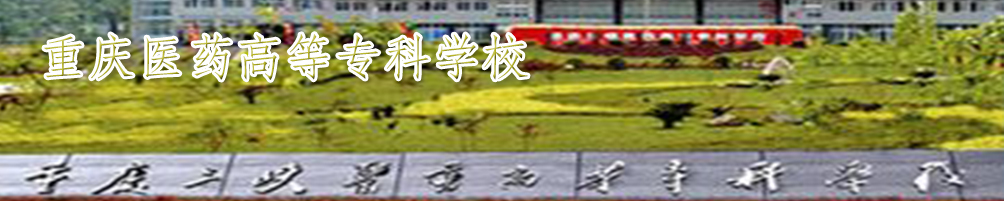
年5月份,我辞职离开北京去到了青海,在果洛州达日县的桑坚珠姆女子慈善学校做志愿者。
在藏地的历史和文化中,有一位犹如璀璨明星一般的传奇女子。她的名字叫做桑坚珠姆。作为西藏历史上伟大英雄格萨尔王的王妃,她凭借着自己超凡的勇气和智慧,在藏族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的背景下,大力提倡女性受教育的权力,是一位真正的自由战士,广泛受到人们的爱戴。因此,桑坚珠姆这个名字,在西藏的文化中,象征着对女性人格的尊重和其生命权利的认可。
彼时,这所桑坚珠姆女子学校创办有10年了,由最初的12个孤儿发展到当时的人,有来自藏区各地的贫困、单亲或孤儿。藏地牧区男尊女卑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,孩子出生养不了的话,男孩子会送去当地寺院出家学习,女孩子就只有留在家里干最苦最累的活,受教育的机会极少。这所学校专门为女子而办,而且是完全免费的。学校的办学目的是让藏族女孩们有一技之长,独立于社会,将来能像桑坚珠姆王妃一样自由和被认可、被尊重。
离学校所在的达日县附近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宁,要坐10个小时大巴。
还记得那天上车点是南川西路客运站,踏入车厢,便被空气中弥漫着的气味熏到,我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,抬头一看,发现大部分乘客都是藏族人。
他们大都穿着藏服,非常好辨识,即使没有穿藏族,皮肤黝黑、五官大气而精致,也是一眼便能分辨出来。那种气味便来自于他们。我放好行李,在前排一个空位坐下,系上安全带时迅速扫瞄了一遍其它乘客们,我好像是唯一一个汉族人。
独身穿梭于另一个民族,这是我喜欢做的。有点害怕也有点兴奋,我和这些陌生人、背景如此不一样的陌生人们,在同一时间踏上这辆班车,我们唯一的共同点是目的地。经常会发自内心的好奇,陌生人啊,你为何而旅行。
那是一种混合着酥油、牦牛肉的膻味,加上没有经常洗澡的习惯而发酵成的一种,藏族人身上特有的气味。未曾想到,那种气味往后在我的生命里,成了最熟悉的气味之一。伴随着这种逐渐熟悉的味道,我很快睡着了,不知过了多久被颠醒了。我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!整个人立刻清醒了,完全沉浸在这满眼的绿色里。
我是谁?我在哪?我要去哪里!
整个旅程持续了10个小时,后面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,突然听到耳边有人说,前面就是达日了。汽车驶入县城时,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全新的世界,街上的建筑都是藏式的,墙上满满的藏式雕花和一些佛菩萨的画像,门店上面挂着藏汉双语的广告牌,街道非常干净。我很喜欢这里。想象中的因贫穷落后而脏乱差根本不存在,甚至,有点精致呢。
这会太阳已经快落山了,我穿上了提前备好的羽绒服,虽是汉地的夏天,高原却已经像深秋。突然有点头疼了,眼皮依旧沉重地想立刻睡去。应该是高反了吧。据说高反在晚上,尤其是后半夜会变得严重。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,有的会头疼到炸裂,有的失眠,吃不下饭,恶心呕吐,等等。
我却是饥饿,还想大睡一觉。下车后搬了下行李箱,我就气喘吁吁了,随后头又是一阵隐痛。依旧是想睡觉。hum…没什么是大睡一觉解决不了的,如果解决不了,那就二觉!
来接我的人到了,带我去吃了当地的四川小炒,点了几个素菜,彼时我还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,朋友说你不吃动物脂肪是很难在高寒地区好好活下去的。我不信,心想偏要试试看。
到达学校提供的宿舍,也不管条件如何,也没有洗漱了,直接倒头就睡!一觉醒来,感到太阳温柔的照在我身上。头也不再疼痛。嗯,达日啊,我终于来了。
这里就是传说中那种连颗树都长不了的地方,更别说开花了。黑黑的牦牛啃着干枯的草竟也能长肉和产奶,当地的藏民们就靠他们生活。大六月的天气,我穿着羽绒服还手脚冰凉。只有中午太阳大的时候才可以洗洗衣服,还得一边祈祷着别突然天降冰雹或狂风暴雨。
除了牦牛制品和青稞,几乎所有物资都是从西宁运过来的,所以物价高得跟帝都有一拼。天空总是湛蓝的,大朵白云飘过,像极了英格兰北部。
初到这里,我受到很大触动。也许是懂得来之不易,女孩们念书很用功,早上5点就起来洗漱,接着是跑操和早读,一直到晚上9点才睡觉。早读和晚读都念得很大声,上课参与的也很认真,求知欲很直接很强烈。
孩子越来越多,校舍一直不够,会出现两个孩子睡一张床的情况。整个学校供电系统设计的不太安全合理,宿舍昏暗,电线裸露在外面。由于冬天气温极低,曾经花巨资安装的暖气系统也被冻坏了,现在教室只能用土炉子取暖,而宿舍里使用的是电暖气片。
在校的孩子里,年龄最小的是6岁最大的是17岁。全校只有一个水龙头,我的宿舍在三楼,每次得下楼提水。太阳很好的时候,全校的孩子会一起洗衣服和洗头,一般是一个大孩子带一个小孩子。这里的女孩,从小都独立。习惯自己来打理一切。
那时,我每个月都会出门一次,每次回来时女孩们都会围上来,看着我说,“老师,我们还以为你走了呢。”女孩们大都拖着长长的鼻涕,见到我,会下意识地猛地吸回去,不好意思地笑。年龄小点的,会把我当妈妈一样抱着不舍得放开,有时也会把我当玩伴,拉着我吹泡泡。一下午经常在阳光和爱里一晃而过,我喜欢被孩子们缠着,幸福无比。
学校的厕所是蹲坑的土厕所。有天早上,年龄最小的达措进来厕所看到我在里面,出去了一下,回来放了一把小石子在我面前,“老师老师给你用。我当时真是又感动又无地自容。我能告诉孩子,老师只习惯用卫生纸吗。
牧区的孩子真正的家还是草原,周末老师们会带大点的孩子们出去爬山或去河边洗头。有一次在爬完山回学校的路上,一个孩子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跟我说:“老师,我来这里之前不开心,现在很开心。”
12月初,我离开如梦如幻的青藏高原,回到云里雾里的大北京。走的那天晚上各种拥抱和祝福,每个孩子都给我写了一封信或画了一幅画,我一晚上没停过流泪。真正要离开才知道自己有多不舍。
回京后我仍然是学校的志愿者,并仍然对之前发起的所有项目负责。往后每年夏天我都会回到学校待个半年,持续帮助这所学校,学校的教学和生活条件明显大大改善了。直到年,这所学校彻底关闭了,原来的学生们也都到申请到了公立学校读书的名额,可谓皆大欢喜。
年初,我关闭了我的禅茶工作室。其实,当时的我早已厌倦大城市的生活,想找个安静的小地方。前几年虽每年在达日短住几个月,我竟然从来没想到长期居住在那里。不过,Whynot?北京的房子退租后,我把所有家当都寄到了达日。
对一个藏区的县城来说,达日已经算相当发达了。比如,这里几乎所有快递都可以寄到,而一般县城基本上只有邮政快递才能到。所以,达日也有“藏地小香港”之称。基本的蔬菜粮油商铺都能买得到,其它的东西淘宝也能搞定。
藏地天气多变,夏天时候,早上还晴空万里,中午突然就开始打雷下雨甚至下冰雹,而傍晚又是晴空万里。总之很难得一整天晴到底。这一秒还穿着衬衣,下一秒或许就需要一个大衣了。我车里常备一件外套。如果是冬天,几乎每天下午都是大风或大雪,出一次门要下好大的决心。
这里虽说有四季更迭,但所谓的夏天,平均温度不到20度;冬天则会降到零下30度,早晚温差很大。这样的气候下,没有树木可以成功长大。风毫无阻碍地侵占着每一寸土地,肆虐无比。
6、7月是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,草长莺飞。那时,我常和男友科智去到草坪,搭个天幕,带上茶具和音响,带一本书,找块河边的平地,一待就是一下午。夏天的夜来的很晚,9点半时,太阳才会完全下山。
当草原上的草开始变黄时,秋天来临,要降温了。但所谓的秋天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比如最近才刚刚进入九月份,就迎来了今年下半年的第一场雪。雨雪天,是适合偷懒、理所应当不需要出门做事的一天。于是我肆无忌惮地宅在家里看书喝茶听音乐。当我忙着拍视频和兴高采烈地晒朋友圈时,科智已经做好了午饭。我们边吃着边商量着,打开地暖吧。这意味着,冬天快要来了。
不过,在今年真正的冬天来临前,我们需要把门窗的漏洞补上。
班玛科智是我年定居达日后交的男朋友,是个达日本地的藏族人,曾经在上海生活过,汉语很好。皮肤黝黑,外形魁梧,天生的一身腱子肉,心思却极细腻。一早突然说要修补门窗,一会就抱着一大堆的建材专用胶和泡沫回来了,还叫上了好兄弟根呷东智帮忙。东智是附近寺院的出家师父,刚20岁,本来在青海省佛学院念书,因为疫情而延迟开学,现在还能一起玩。
高原的建筑材料都是汉地卡车运输过来的,工人也都是青海其余地区或者四川来的,所以盖房子或者装修,都是非常昂贵的。家里有什么需要修的,大家都习惯了自己动手。科智总有各种妙招来搞定各种情况,脑洞无敌大。
在这里生活久了,我接触到一些“达漂”,即达日打工的外来人员。
有一次帮朋友监工盖房子时,认识了来自四川黑水县的夫妇,丈夫叫尼玛,妻子叫卓玛。十几年来,他们每年5月份来达日,10月左右离开,很多施工都要在温度零上才能进行,10月后,达日就要入冬了。
那天的活儿是要用石头砌墙,卓玛是小工,负责搅拌水泥和沙子,一桶一桶提给尼玛,同时需要挑适合尺寸的石头递给尼玛。尼玛是大工,一边把递来的石头放在大小合适的空间,再用铲子把水泥沙子填充满石头之间的缝隙。古时候,藏族人是用石头和泥土混着干稻草来盖,现在有水泥沙子作为材料,盖的比古人的房子坚固多了。
他们配合默契。卓玛熟练的和水泥、挑石头,尼玛总能为递来的石头找到合适的空间。墙砌的非常漂亮。但,随着墙砌的越来越高,卓玛和尼玛的腰也渐渐直不起来了。
高原的太阳,紫外线强,非常刺眼。我在这样的天出门,要涂上厚厚的防晒霜,还要戴上连脖子也全能遮住那种大帽檐的专业防晒帽。有时候还需要戴防晒手套和面罩。当然,不戴墨镜的话,看东西都得眯着眼,眼睛会很不适。可他们夫妇俩,在这样的太阳下,只是简单的戴了劣质的帽子,侧脸对着太阳时,脸和脖子都会被晒到。
卓玛说他们有两个孩子,一个18岁,一个13岁。他们拼命干活,是为了孩子们攒学费。他们的家乡黑水县也属于藏区,相对贫穷。早年间,达日这边有朋友带着他们来“发财”,于是就跟来了,一干就是十几年。谈话间,她反复让我帮他们打听活干。我问,这样干一天,能拿多少钱?她有点自豪地说:一天呢。因此,只要她闲下来哪怕一天,都会感觉心慌。
她恐慌没有活儿干的日子里,焦虑地待在达日租来的小房子里,坐立不安,想着这一天就这么浪费掉,她的孩子因为没有学费而辍学怎么办。想着自己和丈夫为了赚钱而背井离乡,这时却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。
这两年因为疫情影响,达日这边的活儿也没有从前那么多了,活不好找。临走时,她又叮嘱我一定要帮她打听活儿干。“水泥沙子的活儿,都能干”,她看着我,“力气大得很。”我答应她,一定。
陈师傅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电工,大家习惯叫他的藏文名字久美多杰。他说一口流利的藏语,皮肤黝黑。他是达日县电力公司的合同电工,有一次我们学校电路坏了,朋友介绍他来帮忙修。后来,只要学校有电路方面的活儿,都会叫他来。再后来,陈师傅就搬来住在学校了。于是,我们即是邻居又是“同事”。
或许因为我们两人的生活经验差异巨大,几年过去了,交集很少,我们仅有过的对话,大多数是关于学校教室和宿舍的电路走向。对他的个人生活、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我没有任何了解。
前几天,我的电炉炉丝烧断了,便找他帮忙换一根新的。谈话间,他说起自己的女儿前几天上电视了,唱了歌。抬头看我的霎那,我看到一个男人身为人父的温暖笑容,那一刻他眼里有光,笑容里带着小小骄傲,而后又害羞地低下头,继续看着炉子。
我敷衍着说,“这么厉害呀,那她很有音乐天赋吧?”他点点头,“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,这次是代表全校去电视台参加节目的。”
他女儿今年9岁了,在老家和他姐姐住。
十年前,刚结婚的陈师傅,因为想让老婆过上更好的生活,来到达日工作。达日的工资比家乡要高很多。但由于气候条件恶劣,老婆怀孕之后回了老家,生下女儿后也再没来过。前些年,他们一家处于异地状态,但只要一有空,他就会坐上班车回去跟她们团聚。
这种异地状态一直持续到前年,有一天,他接到姐姐的电话,说孩子的妈妈跟了别人,跑了,走之前把孩子交代给她了。他立刻回到老家,四处打听,却怎么也没听到他老婆的下落。亲戚们都劝他放弃这种女人。他回到了达日,埋头工作,接更多的活儿。
讲到这里,他的声音开始哽咽。空气中都凝聚着悲伤。背井离乡来这么艰苦的地方打工,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他的精神支柱,他的一切付出都是为了几个月一次的相聚。但老婆连个预兆都没有,突然跑了。他姐姐说他太善良了,被欺负了。他说,可能人家觉得我还是太穷了吧。
他沉浸在回忆中,诉说着他的孤独和伤心往事。我专心听着,没有感到厌烦,也没有因为缓解尴尬气氛而进行这场对话的感觉。或许,这是对此刻的他最好的尊重。我想,此时此刻,我不需要建议他在达日找个对象,不需要给他分析异地恋多么的不靠谱,更不需要说单身挺好这种鬼话。而只需要静静地听着,发出语气词简单回应就好。
对于一个经验老道的电工来说,安装炉丝实在太简单了。他很快就搞定了。通上电,炉丝渐渐变红,可以用了。我向他道谢,就像每一次他帮我们修好了电路一样。四目对时,他整个人轻松了许多,身在异乡为异客,或许,有些痛苦和无奈,他只能强压在心底,无处倾诉。
我感到我第一次认识了他这个人,不再是“学校的电工陈师傅”,更像是,交了一个新朋友。我明白那种信任来之不易,也为自己过去的傲慢而感到羞耻:他出身农村,没什么文化,后来跟了师傅学电工,整个人的社会层次不算高,是我不会主动搭话的群体,更不会去主动交朋友。今天,因为信任,他把他的孤独毫无保留给展露给我,那种坦然和真诚深深触动了我,融化了我这颗生硬的心,也融化了我的傲慢。
原标题:《藏地生活这七年
三明治》